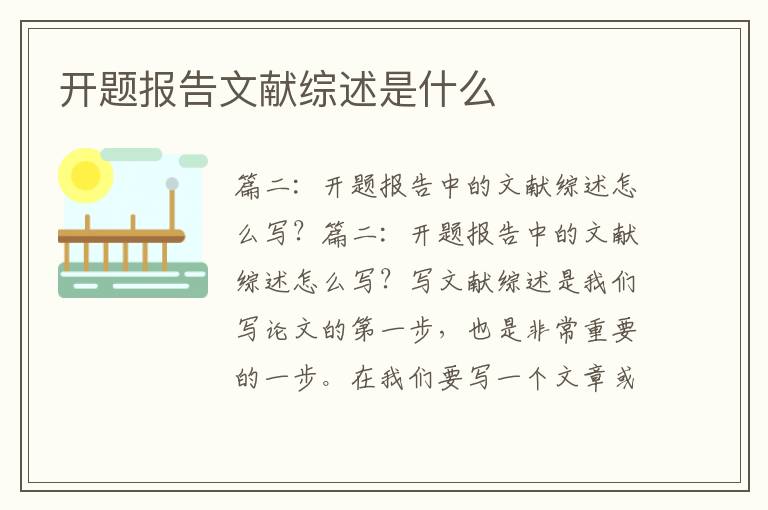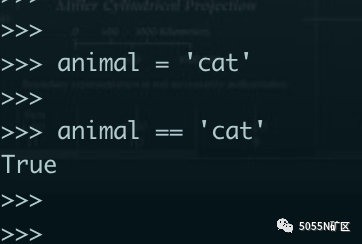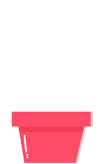我怎樣寫(xiě)小說(shuō)


大多數(shù)的小說(shuō)里都有一個(gè)故事,所以我們想要寫(xiě)小說(shuō),似乎也該先找個(gè)故事。
找什么樣子的故事呢?從我們讀過(guò)的小說(shuō)來(lái)看,什么故事都可以用。戀愛(ài)的故事、冒險(xiǎn)的故事固然可以利用,就是說(shuō)鬼說(shuō)狐也可以。故事多得很,我們無(wú)須發(fā)愁。
不過(guò),在說(shuō)鬼狐的故事里,自古至今都是把鬼狐處理得像活人;即使專(zhuān)以恐怖為目的,作者所想要恐嚇的也還是人。假若有人寫(xiě)一本書(shū),專(zhuān)說(shuō)狐的生長(zhǎng)與習(xí)慣,而與人無(wú)關(guān),那便成為狐的研究報(bào)告,而成不了說(shuō)狐的故事了。由此可見(jiàn),小說(shuō)是人類(lèi)對(duì)自己的關(guān)心,是人類(lèi)社會(huì)的自覺(jué),是人類(lèi)生活經(jīng)驗(yàn)的紀(jì)錄。那么,當(dāng)我們選擇故事的時(shí)候,就應(yīng)當(dāng)估計(jì)這故事在人生上有什么價(jià)值,有什么啟示;也就很顯然的應(yīng)把說(shuō)鬼說(shuō)狐先放在一邊——即使要利用鬼狐,發(fā)為寓言,也須曉得寓言與現(xiàn)實(shí)是很難得諧調(diào)的,不如由正面去寫(xiě)人生才更懇切動(dòng)人。

依著上述的原則去選擇故事,我們應(yīng)該選擇復(fù)雜驚奇的故事呢,還是簡(jiǎn)單平凡的呢?據(jù)我看,應(yīng)當(dāng)先選取簡(jiǎn)單平凡的。故事簡(jiǎn)單,人物自然不會(huì)很多,把一兩個(gè)人物寫(xiě)好,當(dāng)然是比寫(xiě)二三十個(gè)人而沒(méi)有一個(gè)成功的強(qiáng)多了。寫(xiě)一篇小說(shuō),假如寫(xiě)者不善描寫(xiě)風(fēng)景,就滿可以不寫(xiě)風(fēng)景,不長(zhǎng)于寫(xiě)對(duì)話,就滿可以少寫(xiě)對(duì)話;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,沒(méi)有人便沒(méi)有事,也就沒(méi)有了小說(shuō)。創(chuàng)造人物是小說(shuō)家的第一項(xiàng)任務(wù)。把一件復(fù)雜熱鬧的事寫(xiě)得很清楚,而沒(méi)有創(chuàng)造出人來(lái),那至多也不過(guò)是一篇優(yōu)秀的報(bào)告,并不能成為小說(shuō)。因此,我說(shuō),應(yīng)當(dāng)先寫(xiě)簡(jiǎn)單的故事,好多注意到人物的創(chuàng)造。試看,世界上要屬英國(guó)狄更斯的小說(shuō)的穿插最復(fù)雜了吧,可是有誰(shuí)讀過(guò)之后能記得那些勾心斗角的故事呢?狄更斯到今天還有很多的讀者,還被推崇為偉大的作家,難道是因?yàn)樗墓适聫?fù)雜嗎?不!他創(chuàng)造出許多的人哪!他的人物正如同我們的李逵、武松、黛玉、寶釵,都成為永遠(yuǎn)不朽的了。注意到人物的創(chuàng)造是件最上算的事。
我說(shuō)寫(xiě)小說(shuō)應(yīng)先選擇個(gè)故事。這也許小小的有點(diǎn)語(yǔ)病,因?yàn)樵谑聦?shí)上,我們寫(xiě)小說(shuō)的動(dòng)機(jī),有時(shí)候不是源于有個(gè)故事,而是有一個(gè)或幾個(gè)人。我們倘然遇到一個(gè)有趣的人,很可能的便想以此人為主而寫(xiě)一篇小說(shuō)。不過(guò),不論是先有故事,還是先有人物,人與事總是分不開(kāi)的。世界上大概很少?zèng)]有人的事,和沒(méi)有事的人。我們一想到故事,恐怕也就想到了人,一想到人,也就想到了事。我看,問(wèn)題倒似乎不在于人與事來(lái)到的先后,而在于怎樣以事配人,和以人配事。換句話說(shuō),人與事都不過(guò)是我們的參考資料,須由我們調(diào)動(dòng)運(yùn)用之后才成為小說(shuō)。

比方說(shuō),我們今天聽(tīng)到了一個(gè)故事,其中的主人翁是一個(gè)青年人。可是經(jīng)我們考慮過(guò)后,我們覺(jué)得設(shè)若主人翁是個(gè)老年人,或者就能給這故事以更大的感動(dòng)力;那么,我們就不妨替它改動(dòng)一番。以此類(lèi)推,我們可以任意改變故事或人物的一切。這就仿佛是說(shuō),那足以引起我們注意,以至想去寫(xiě)小說(shuō)的故事或人物,不過(guò)是我們主要的參考材料。有了這點(diǎn)參考之后,我們須把畢生的經(jīng)驗(yàn)都拿出來(lái)作為參考,千方百計(jì)地來(lái)使那主要的參考豐富起來(lái),像培植一粒種子似的,我們要把水分、溫度、陽(yáng)光……都極細(xì)心調(diào)處得適當(dāng),使它發(fā)芽,長(zhǎng)葉開(kāi)花。總而言之,我們須以藝術(shù)家自居,一切的資料是由我們支配的;我們要寫(xiě)的東西不是報(bào)告,而是藝術(shù)品——藝術(shù)品是用我們整個(gè)的生命、生活寫(xiě)出來(lái)的,不是隨便地給某事某物照了個(gè)四寸或八寸的相片。我們的責(zé)任是在創(chuàng)作:假借一件事或一個(gè)人所要傳達(dá)的思想,所要發(fā)生的情感與情調(diào),都由我們自己決定,自己執(zhí)行,自己做到。我們并不是任何事任何人的奴隸,而是一切的主人。
遇到一個(gè)故事,我們須親自在那件事里旅行一次,不要急著忙著去寫(xiě)。旅行過(guò)了,我們就能發(fā)現(xiàn)它有許多不圓滿的地方,須由我們補(bǔ)充。同時(shí),我們也感覺(jué)到其中有許多事情是我們不熟悉或不知道的。我們要述說(shuō)一個(gè)英雄,卻未必不教英雄的一把手槍給難住。那就該趕緊去設(shè)法明白手槍?zhuān)瑒e無(wú)辦法。一個(gè)小說(shuō)家是人生經(jīng)驗(yàn)的百貨店,貨越充實(shí),生意才越興旺。

旅行之后,看出哪里該添補(bǔ),哪里該打聽(tīng),我們還要再進(jìn)一步,去認(rèn)真地扮作故事中的人,設(shè)身處地地去想象每個(gè)人的一切。是的,我們所要寫(xiě)的也許是短短的一段事實(shí)。但是,假若我們不能詳知一切,我們要寫(xiě)的這一段便不能真切生動(dòng)。在我們心中,已經(jīng)替某人說(shuō)過(guò)一千句話了,或者落筆時(shí)才能正確地用他的一句話代表出他來(lái)。有了極豐富的資料,深刻的認(rèn)識(shí),才能說(shuō)到剪裁。我們知道十分,才能寫(xiě)出相當(dāng)好的一分。小說(shuō)是酒精,不是摻了水的酒。大至歷史、民族、社會(huì)、文化,小至職業(yè)、相貌、習(xí)慣,都須想過(guò),我們對(duì)一個(gè)人的描畫(huà)才能簡(jiǎn)單而精確地寫(xiě)出,我們寫(xiě)的事必然是我們要寫(xiě)的人所能擔(dān)負(fù)得起的,我們要寫(xiě)的人正是我們要寫(xiě)的事的必然的當(dāng)事人。這樣,我們的小說(shuō)才能皮裹著肉,肉撐著皮,自然的相連,看不出虛構(gòu)的痕跡。小說(shuō)要完美如一朵鮮花,不要像二黃行頭戲里的“富貴衣”。
對(duì)于說(shuō)話、風(fēng)景,也都是如此。小說(shuō)中人物的話語(yǔ)要一方面負(fù)著故事發(fā)展的責(zé)任,另一方面也是人格的表現(xiàn)——某個(gè)人遇到某種事必說(shuō)某種話。這樣,我們不必要什么驚奇的言語(yǔ),而自然能動(dòng)人。因?yàn)楣适轮械膶?duì)話是本著我們自己的及我們對(duì)人的精密觀察的,再加上我們對(duì)這故事中人物的多方面想象的結(jié)晶。我們替他說(shuō)一句話,正像社會(huì)上某種人遇到某種事必然說(shuō)的那一句。這樣的一句話,有時(shí)候是極平凡的,而永遠(yuǎn)是動(dòng)人的。我們寫(xiě)風(fēng)景也并不是專(zhuān)為了美,而是為加重故事的情調(diào),風(fēng)景是故事的衣裝,正好似寡婦穿青衣,少女穿紅褲,我們的風(fēng)景要與故事人物相配備——使悲歡離合各得其動(dòng)心的場(chǎng)所。小說(shuō)中一草一木一蟲(chóng)一鳥(niǎo)都須有它的存在的意義。一個(gè)迷信神鬼的人,聽(tīng)了一聲?shū)f啼,便要不快。一個(gè)多感的人看見(jiàn)一片落葉,便要落淚。明乎此,我們才能隨時(shí)隨地的搜取材料,準(zhǔn)備應(yīng)用。當(dāng)描寫(xiě)的時(shí)候,才能大至人生的意義,小至一蟲(chóng)一蝶,隨手拾來(lái),皆成妙趣。
以上所言,系對(duì)小說(shuō)中故事、人物、風(fēng)景等作個(gè)籠統(tǒng)的報(bào)告,以時(shí)間的限制不能分項(xiàng)詳陳。設(shè)若有人問(wèn)我,照你所講,小說(shuō)似乎很難寫(xiě)了?我要回答也許不是件極難的事,但是總不大容易吧!
選自《老舍全集》